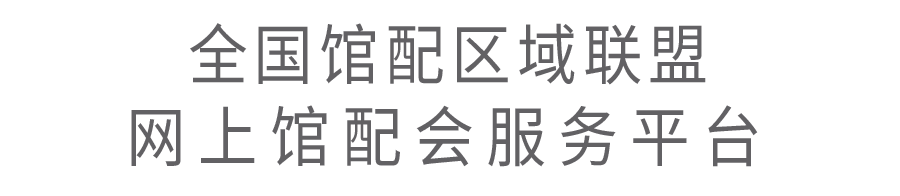Ą¶ś{ô~œÖĄ·ŚgșóÓ
îÏòs
ŠČŒôÖZ·Êæ ŽÄ”ÄçÇéÊŒÓÚ20ÊÀŒo(jšŹ)90ÄêŽúĄ¶ÍâűÎÄËĄ·ÉÏżŻ”Ç”ÄÓÚÄŹÏÈÉú·Śg”ÄŚÆȘËû”ÄĐĄŐf����ŁŹÎÒӔß(dšĄng)rÊÇŐŸÔÚW(xušŠ)ĐŁéÓ[ÊÒűŒÜß^”ÀÀïșöÈ»żŽ”œĄ¶űBĄ·șÍĄ¶óŻò륷”ÄŁŹžĐÓXË(bišĄo)î}¶ŒÊÇĐĄÓÎïĐĄÀ„Ïx��ĄŁŚxÁËÆŹżÌșó���ŁŹČ»ÖȘÓÉÓÚÉÏŐnßÊÇÒȘžÉe”ÄÊČĂŽÊÂș�����ŁŹÎÒŽÒŽÒëxé_éÓ[ÊÒ�����ŁŹÄÄÇÒÔșóŸÍÔÙ]ÓĐżŽ”œÄDZŸësÖŸ����ŁŹčÜDű”ÄÌKÀÏŐfÓĐÒ»ĆúësÖŸÙuœoÍâĂæ”ÄÈËÁËĄŁÎÒÏëțČ»țÂ䔜ÔÚ±±Žó|éTÍâ[ű”ÄÄÇĐ©ÈËÊÖÀïÁË�ĄŁŽËșóŁŹĐÄÀïČ»r”ëÄîÖűÄÇŚË(bišĄo)î}čÖč֔ĶÌÆȘ����ĄŁÒČÔSß@·N”ëÄîÒâζÖűÊæ ŽÄŚîœKțžúÎÒÓĐêP(gušĄn)ĄŁșóí���ŁŹÄ·ÆÀûÆŐ·Á_ËŒ”ÄÒ»±ŸÔuŐŚśŒÒ”ÄĐĄűÀïżŽ”œËûŠÊæ ŽÄ·ÇłŁžĐĆdÈ€����ŁŹÔűŁéTŽòëÔŒs°ŹË_żË·°ÍÊČŸSËč·ĐÁžńŐ?wšŽ)ÍŹÊÇČšÌmÈË”ÄÊæ ŽÄ����ĄŁŚxÍêß@ÆȘÎÄŐÂșóÎÒČĆ°l(fšĄ)ŹF(xiš€n)ß@Àï”ÄÊæ ŽÄŸÍÊÇÎÒÀÏ”ëÓ”ÄÄÇÊæ ŽÄĄŁÓÚÊÇńRÉÏŐÒíÊæ ŽÄ”ÄŚśÆ·�ŁŹŚșőČ»ÓÉ·ÖŐfŸÍ·ŚgÆđíŁŹÒČČ»ÓĘ^ÄÜ·ń°l(fšĄ)±í���ĄŁ·Śgß@±ŸÖ»ÓĐ20ÈfŚÖ”ĶÌÆȘĐĄŐfŒŻ����ŁŹêÀm(xšŽ)»šÁËșÜéLrégŁŹ·ŽÍ(fšŽ)ĐȚžÄÁ˶à±é��ĄŁ”«ÊÇ���ŁŹŹF(xiš€n)ÔÚżŽíŁŹoŐĐȚžÄ¶àÉÙ±é����ŁŹß@čĆčÖŽóżÓĐÒ»·NżčŸÜÎҔȷČÈËßM(jšŹn)ÈëËû”ÄÊÀœç”ÄÉńĂŰÁŠÁżĄŁÎÒÏë���ŁŹÒȘžúËû”Äß@čÉÉńĂŰÁŠÁżŚœĂÔČŰ�����ŁŹÎÒĐèÒȘoÏȚ”Ű·ŚgÏÂÈ„�����ĄŁ
Ó”ĂÓĐλÎïÀíW(xušŠ)ŒÒŐfß^���ŁŹÓîÖæ±ÈÎÒÏëÏó”ÄÒȘžüŒÓčĆčÖĄŁß@ŸäÔÓĂÔÚÊæ ŽÄ”ÄĐĄŐfÉÏÍŹÓßmșÏŁșÊæ ŽÄ”ÄŚśÆ·ÒȘ±ÈÎÒÏëÏó”ÄžüŒÓčĆčÖĄŁß@λŚăČ»łöô”ĶÌÆȘĐĄŐfŽó����ŁŹÔÚČšÌmijХłÇÒ»Ž±§”êä”Äč«ÔąÇÀï IÔìÖűœüșőÏëÈë·Ç·Ç”ÄÊÀœçŁŹÔÚ”êäéwÇÉÏ°ČìoÓÖœč]”ŰÓ^ČìșÍA ÖűÈfÎï”ÄŒ(xšŹ)ÎąÓìo����ĄŁÔÚËû”Ķú¶äÂ íŁŹÈfÎï”ÄĘpŐZŒŽÊÇĐúW��ŁŹìoÖk”ÄÈäÓÂÖĐ°”ČŰÖűÊÀœç”Äò}Ó�����ĄŁËûÔDÏòÎÒœÒé_ŹÊ±łșóÈf»šÍČ°ă”ÄÆæĂîŸłœç�����ĄŁ
Êæ ŽÄÓÚ1892Äê7ÔÂ12ÈŐÉúÓÚČšÌm”Ä”ÂÁ_žêŰÆæĐĄłÇ���ĄŁžžÓHÊÇČŰűŒÒ��ŁŹœ(jš©ng) IÒ»ŒÒÒÂÁÏä���ŁŹß@äŚÓșóíÔÚșŚÓ”ÄŚśÆ·ÖĐłÉéÙAČŰ»ĂÏë”Ä}ì��ŁŹŽæ·ĆÉńÔ”ÄĂÜÊÒ�ĄŁÊæ ŽÄW(xušŠ)ß^ÈęÄꜚÖț���ŁŹŚÔW(xušŠ)ÀLź����ŁŹŚîœKŚöÁËÒ»ĂûÖĐW(xušŠ)ĂÀĐg(shšŽ)œÌ�ĄŁËûÄ20ÊÀŒo(jšŹ)20ÄêŽúé_ÊŒĂÈÉúĐĄŐf”ÄÄîî^����ŁŹÏëÓĂÎÄW(xušŠ)(chuš€ng)ŚśíŐ{(diš€o)©ÎŐ{(diš€o)żĘÔï”ÄÉú»îĄŁŒ{ŽâŐŒîI(lš«ng)čÊàl(xišĄng)ĐĄłÇșó�ŁŹËû±»ŽòËÀÔÚœÖî^ŁŹrÄê50q��ĄŁß@ÏàĂČÆæÌŰ����ĄąÉńB(tš€i)ăŸăČŁŹéLÖűÒ»Én°Ś”ÄÈęœÇÄșÍÒ»ëp°ŒÏÂÈ„”ÄŚŰÉ«ŃÛŸŠ�ĄąÊĘčÇáŚáŸ”ÄÈËŁŹșóíłÉÁËČšÌmÎÄW(xušŠ)Ê·ÉÏȘŽËÒ»ŒÒ”ÄŽó���ŁŹ”«ÊÇșÜéLÒ»¶Îrég�����ŁŹ]ÈËÖȘÔËûÊÇșÎÔSÈË��ĄŁËû”ÄŚśÆ·ŽóÖÂÔÚ20ÊÀŒo(jšŹ)60ÄêŽúČĆé_ÊŒéÎś·œËùÁËœâ���ŁŹ”Ă”œ±¶àŚxŐß”ÄÙÙp���ŁŹÈ»¶űÈË
sČ»ÖȘ”ÀÈçșÎíêUáËû”ÄŚśÆ·ĄŁ
ț(jšŽ)Őf���ŁŹÊæ ŽÄłŁÄêÉú»îÔÚčÂȘÖĐ����ŁŹëxÈșËśŸÓ����ŁŹłÁŚíÔÚŚÔŒș”ÄôÏëșÍÍŻÄê”Ä»ŰÖĐŁŹß^ÖűŸo¶űÌŰź”ÄÈ(nšši)ĐÄÉú»î��ŁŹŠÎïÙ|(zhšŹ)ÊÀœç”ÄŽÌŒ€·ŽȘ(yš©ng)ĂôžĐ¶űÓÖÁÒ���ĄŁÎÒÔÚÊæ ŽÄ”ÄĐĄŐfÖĐČ»ëyżŽłö��ŁŹËûëSĐÄËùÓû”Ű°ČĆĆrég”ÄÁśÊĆ�ŁŹŚ»ĂÏëÊÀœçŚ?yšu)éŹF(xiš€n)ĄŁËû(chuš€ng)ÔìłöÒ»șÜΚÎÒ”ÄÉńÔÊÀœç����ŁŹÏûćôÁËë[ĂŰ”ÄŸ«Éń»îÓĆcÍâÔÚŹF(xiš€n)ÖźégĄąÀíÖÇĆcÇéžĐÖźég”ÄœçÏȚ��ĄŁQŃÔÖź��ŁŹËûÒȘ»Ű”œÔÒâ”ÄŚîÉîÌ�����ĄŁËûÒȘ±íŹF(xiš€n)ÎҔČŻówÏëÏó�����ĄąËü”ıŸÙ|(zhšŹ)ÒȘËŰșÍCÖÆ�����ĄŁËû”ÄÊÀœçÀ(yšąn)žńŚńŐŐÒ»șąŚÓ”ÄÔÒâĐÄÀíłß¶È���ŁŹłäMÁËžś·NžśÓ”Äë[Óś�����ĄŁß@ÊÀœçÓÁŠ”ÄÔŽÈȘŸÍÊÇÉńÆæ”ÄÏëÏóÁŠ����ŁŹß@Ó”ÄÏëÏóÁŠoŐœ(jš©ng)ß^¶àĂŽO¶Ë”ÄŹF(xiš€n)»ŻÒČČ»țżĘÎź����ĄŁĐÁžńŐfËûÓĐrșò?qš±)”ĂÏńżš·òżšŁŹÓĐrșòÏńÆŐôËčÌŰ�ŁŹ¶űÇÒœ(jš©ng)łŁłÉ芔Űß_(dšą)”œËû]ÓĐß_(dšą)”œ”ÄÉî¶ÈĄŁÊæ ŽÄ”ÄŚśÆ·ÖśÒȘÊÇɱŸ¶ÌÆȘĐĄŐfŒŻĄ¶ś{ô~œÖĄ·șÍĄ¶ÓĂɳ©ŚöŐĐĆÆ”ÄŻđB(yšŁng)ÔșĄ·�����ŁŹÁíÓĐÈôžÉűĐĆșÍÒ»ĆúÀLź�ĄŁț(jšŽ)ŐfŁŹÊæ ŽÄ”Ä(chuš€ng)Śś»òŐßà«à«ŚÔŐZó@ÓÁËßh(yušŁn)ÔÚÓąű”ÄÒâŚRÁśŽóŐČÄ·Ëč·ÌÒÁËč����ŁŹËûÉőÖÁĂÈÓÁËW(xušŠ)Á(xšȘ)ČšÌmŐZ”ÄÏë·šŁŹÒȘÓHŚÔŚßßM(jšŹn)Êæ ŽÄ”ÄÊÀœçżŽżŽ���ĄŁ
Êæ ŽÄ IÔì”ÄÄÇÊÀœç”ÄÖĐĐÄÈËÎïŸÍÊÇłÁœțÔÚô»ĂÖДĞžÓH��ĄŁËû”ÄÈ«ČżĐĄŐfżÓÓĐ29ÆȘ����ŁŹÆäÖĐÖ±œÓ”œžžÓH”ÄÓĐ10ÆȘŁŹÁíÍâÓĐŚÆȘégœÓ”ŰÌᔜÁËžžÓH���ĄŁß@10ÆȘĐĄŐfȘqÈçÒ»ĐĄÏ”ÁĐ��ŁŹżÌźÁË»ÄŐQČ»œ(jš©ng)”ÄžžÓH���ŁŹÙÓÚÊæ ŽÄ¶ÌÆȘÖĐ”ÄŸ«Æ·ĄŁ
žžÓH”ÚÒ»ŽÎłööÊÇÔÚĄ¶Ê„ï@Ą·Àï�ĄŁß@ÊÇÒ»ĆeÖččĆčÖĄąÉúĂüÁŠÖđuÎźżs”ÄžžÓH����ĄŁËûÓĐÒ»čÉÁÒ”Ä_Ó�ŁŹÏŁÍûŚłÉČ»ÊÇŚÔŒș”ÄÄÇ·NÊÂÎïŁŹßh(yušŁn)ëxÈËîŒŻów�����ĄŁËûÈ(nšši)ĐÄČ»àĆcŒÙÏëŠÊÖșÍÉϔی€ȚqŁŹœ(jš©ng)łŁà«à«ŚÔŐZ����ŁŹČ»ÖȘËùÔÆŁŹœ(jš©ng)łŁëxé_·żég¶ăÔÚč«ÔąČ»éÈËÖȘ”ÄœÇÂä�����ŁŹČ»ÖȘËùœK�����ĄŁ
ÔÚĄ¶űBĄ·ÖĐ�����ŁŹ¶ŹÈŐíĆR����ŁŹžžÓH”ÄĐĐéžüŒÓčÖŐQŁŹËûÓĐr·âÆđ tŚÓŃĐŸżŚœĂțČ»¶š”Ä»đŃæ����ŁŹÓĐrŐŸÔÚ¶ÌÌĘÉÏŃöÒÆáÓĐÌìżŐșÍűBșD°ž”ÄÌ컚°ćŁŹÓĐr°Ń¶ú¶äÙNÔڔ۰ć”ÄÁŃżpÉÏńö ŁŹÓĐrÈç°VÈçŚí”ŰÓ^żŽĆźÆÍŽòß·żég��ĄŁËûŃÖűËĐg(shšŽ)ŒÒ”ÄŒ€Çé����ŁŹÔÚéwÇÉÏ·őűBŁŹĆàđB(yšŁng)łöžś·NžśÓÆæĐÎčÖ î”ÄűBș���ŁŹœšÁąÆđÒ»ŚÔŒșȘÏí”ÄűBș”ÄÍőű��ĄŁžžÓHËùÓĐß@Đ©»ÄŐQĆeÖ豳șó͞¶łö”ÄËÆșőÊÇŠŹF(xiš€n)ÊÀœçÎŐ{(diš€o)·ŠÎ¶”Ä·Žżč����ŁŹÏëÓĂÔÒâ”ÄÏëÏó(gš°u)ÔìŚÔŒș”ÄÍőű��ĄŁŚîœK����ŁŹß@ÔÒâÍőű
s±»ĆźÆÍÓĂßÖă§çÁËŁŹÄÇÈșÓđĂ«ÓÎïÌűÖű§ç”ÄÎ蔞ëxé_éwÇïwÏòÁËßbßh(yušŁn)”ÄÌìżŐ��ĄŁ
”œÁËĄ¶ČĂżp”ÄČŒÍȚÍȚĄ·����ŁŹêöČÔÙŽÎÇÖÒułÇÊĐŁŹÔÚß@¶Î»èłÁoÁÄ”ÄÈŐŚÓ�ŁŹžžÓHoÒâÖĐĆöÉÏÉÓĂËéČŒÆŹżpÖÆČŒÍȚÍȚ”ÄÄêĘpĆźČĂżpĄŁĐĄŐfÍšÆȘÊÇžžÓHÔÚÒčégŠČĂżp���ĄąĆźÆÍ°ą”ÂÀșÍșŚÓŃĘÖvŚÔŒșŚÁÄ„łöí”Ä(chuš€ng)ÊÀÀíŐŁșłęÁËÉÏ”Û�ŁŹĂżÈ˶ŒżÉÒÔ
ąĆcÈfÎï”Ä(chuš€ng)Ôì����ĄŁÈfÎï”Ä(chuš€ng)ÔìŒÙÎïÙ|(zhšŹ)ŚÔÓÉß\ÓĄąĂ€Äż(gš°u)Ôìłöí”Ä�����ĄŁÉúĂüĐÎÊœ”Ä·NîǧČîÈfe��ŁŹožFo±M���ŁŹÖ»ÒȘœoÎïÙ|(zhšŹ)ČÄÁÏÙxÓèÒ»·NĐÎÊœŸÍżÉÒÔ(chuš€ng)ÔìłöÒ»·NÉúĂü����ĄŁ
Ą¶ÈâčđÉ«äŚÓĄ·žúžžÓH”ÄêP(gušĄn)Â(lišąn)ÂÔÎąégœÓ�����ĄŁß@ÀïÌᔜÁËžžÓH”ÄÓŚÓŁșMÄyĆîĆÓČÔúÔú”ĻҰl(fšĄ)�����ŁŹyÆß°ËÔă”ŰÄđàŚÓÉÏ�ĄąĂŒĂ«ÖĐĄą±ÇżŚÀïă@łöí����ĄŁß@ÊÇÒ»ïL(fš„ng)”ÄïSïSÂĄąșÚÒč”ÄÖšÖšžÂžÂÂÒÔŒ°”Ű°ćÉÏĂŰĂÜÒ§§ÉúŃÄ”Äńö ŐßșÍÓ^ČìŒÒ��ĄŁĐĄŐfÓĂÁËÈę·ÖÖź¶ț”ÄÆȘ·ùĂèÉÙÄêÔÚÔÂÒčËùœ(jš©ng)v”ÄÒ»ÇĐ�����ĄŁß@ÊÇÒ»ŽÎ·ÇłŁĂÀĂî”Äówò�����ŁŹ”«œoÉÙÄê§íŚîĂÀșĂ”Äówò
sÊÇÄÇĐ©ÔÚÒčégßé_Öű”ÄÈâčđÉ«”ÄäŚÓ��ĄŁŚśŐߊÒčÍí”Ä»ĂŸ°O±MäêÖźÄÜÊÂ�ŁŹśß_(dšą)ÁËÒčégčâÓ°”ÄĂÔmëyÒÔŃÔś”ÄśÈÁŠŁŹ”«§ÓĐÉÙÄêÁÒ”ÄÖśÓ^Ć€ÇúÉ«ČÊ�����ĄŁ
Ą¶óŻò륷ÀïžžÓHËÆșőÒŃœ(jš©ng)È„ÊÀ�����ŁŹ”«ÊÇßBÉúËÀß@°ăŽóÊÂÔÚĐĄŐfÖĐÒČŚ”ĂÄŁÀâÉżÉ�����ŁŹșŚÓÓX”ĂžžÓHŚłÉÁË[ÔÚŒÒÀï”ÄÄÇŒț¶dú”ÄË(bišĄo)±Ÿ���ŁŹŃÛŸŠÒŃœ(jš©ng)ĂÂä�����ŁŹÄŸĐŒÄŃÛŽüÀïÈöłö���ĄŁžžÓH”ÄËÀÈ„ĆcÒ»ŽÎóŻòë”ÄŽóÒ(guš©)ÄŁÈëÇÖ”Äó@șÍëSÖźźa(chšŁn)Éú”ÄÔśșžĐÓĐêP(gušĄn)ŁŹß@·NÔśșžĐŚîșóŰ”ŚșÄœßÁËžžÓH”ÄŸ«ÁŠ����ŁŹŚîșóßBžžÓH±ŸÈËÒČËÆșőÖđuŚłÉÁËóŻò룏é_ÊŒß^ÆđóŻòë”ÄÉú»î�ŁŹÈ«ĐÄÈ«Òâ”ŰžÉÖűóŻòëžÉ”ÄÊÂÇé�����Ą���ŁżÉÊÇÄžÓH
sÔłÖŐfžžÓHß»îÖűŁŹÖ»ÊÇÔÚÈ«űžś”ŰŚöÖűÂĂĐĐÍÆäN而ś�ŁŹÓĐrÉîÒč»ŰŒÒŁŹÌìÁÁÇ°ÓÖŚßÁË��ŁŹÔÚß@Àï���ŁŹžžÓH”ÄÉúËÀłÉéČ»Ž_¶š”ÄëyœâÖźÖi�����ĄŁ
Ą¶ÊąŒŸÖźÒ襷ÓĂŽóÁż”ÄčPÄ«äÖÈŸÁËÒ»·ŹžžÓH”êäÀï”Ä·Őú��ŁŹÆäÖĐŚîŒŃ”ÄäÖÈŸÄȘß^ÓÚŠ”êÀïČŒÁÏ”ÄĂèÀL��ŁŹß@Đ©ÎćîÁùÉ«”ÄČŒÁÏÔÚžžÓH»òŐßșŚÓŃÛÖĐÍêÈ«ÊÇÇ Êìœkû”ÄïL(fš„ng)Ÿ°ź����ĄŁß@·N»ĂÓX”ĂĂÀČ»ÙÊŐ�ĄŁžžÓH°Ńß@ÆŹłÁìo”ÄîÉ«ÊÀœçżŽ”ĂŚăŐäÙF�ŁŹÉúĆÂÔ├һœzÆÆÄ��ĄŁ”«ÊÇÊąŒŸÖźÒč”œíÁË���ŁŹÒ»ÈșÈșșôș°ÖűÒȘŚöÙIÙu”ÄÈËČ»à_ô”ê䣏°Ń”êÀï”ÄČŒÁÏÍÆ”č���ŁŹČŒÁÏÉąÂäé_í�ŁŹÄÇœkû”ÄÉ«ČÊȘqÈçșéÁś°ăAa¶űłö�ŁŹß@ržžÓHÏńÌĂŒȘÔX”°ăŐŸÔÚČŒÁÏÉÏ]ÎèÖűĆ”ÄÈî^żčôÄÇĐ©ÆÆÄČŒÁÏîÉ«ĂÀŸ°”ÄÈșĂ„”Äúč„ĄŁÔÚžžÓHŚîĐèÒȘ”Ärșò����ŁŹËû”Ä»ïÓ
sÔÚŒÒÀïŚ·ÖđĂÀû”ÄĆźò°ą”ÂÀĄŁžžÓHÔÚșŽĐl(wšši)ŚÔŒșÔÒâÊÀœç”Äœč]șÍŒ”¶Ê»ïÓ”ÄÇéÓûŒć°ŸÖĐŚșőÒȘ±ÀąÁË��ĄŁß@öïL(fš„ng)ČšÆœÏą����ŁŹÌìżŐÖĐșöÈ»łöŹF(xiš€n)ÁËŽóÁżÆæź”ÄűBŚćŁŹÔÚżŐÖĐí»ŰïwÏè±P»ž��ĄŁ”«ÊÇ����ŁŹß@Đ©űBș¶ŒÊÇ»ûĐΔÄ���ŁŹÓĐ”ÄéLÖűÉÄXŽüŁŹÓĐ”ÄÓĐșܶàłá°ò��ŁŹÓĐ”ÄÄ_ÊÇőË”Ä���ŁŹ¶Œ°l(fšĄ)Óę”ĂłóÂȘČ»ż°���ŁŹžčÈ(nšši)żŐżŐÊÊŁŹ]ÓĐŐæŐę”ÄÉúĂü���ĄŁ”«ÊÇß@Đ©űBșșÜżìŸÍ±»ÈșĂ„ÓĂÊŻî^ÔÒÁËÏÂí�ŁŹŚłÉÒ»¶Ń¶ŃÓđĂ«șÍÖ«ów”ÄËéÆŹ�����ŁŹÉąÂäÔÚ”ŰĂæ�ĄŁß@Đ©űBșÆäÊÇžžÓHŚÄêÇ°ÔÚéwÇíÓĆàÓ꣏±»°ą”ÂÀÚsŚß�ŁŹœ(jš©ng)ß^ÈôžÉÊÀŽúșóÓÖïw»ŰčÊ@”ÄÄÇĆúűBșĄŁß@ŽÎűBș”ÄÒâÍâwíÁîžžÓHŒ€ÓČ»ÒŃ�����ŁŹ”«ËüŚîœKßÊÇçœ^ÔÚÈËî”ÄżáÊÖÖźÖĐĄŁÔÚß@ÊąŒŸÖźÒč���ŁŹžžÓHœ(jš©ng)vÁËÉöŸȚŽó”ÄÄ(zšĄi)Ś��ŁŹoŐËûœ(jš©ng) I”ÄîÉ«ĂÀŸ°ßÊÇČ»ÆÚ¶űÖÁ”ÄÌì»[°ă”Ä»ÄŐQ���ŁŹ¶Œ±»§çÁË��ĄŁ
ÔÚĄ¶žžÓHŒÓÈëÁËÏû·Àê Ą·ÖĐ��ŁŹ»ÄŐQ”ÄžžÓHŽ©ÉÏżűŒŚ°ŃŚÔŒșŽò°çłÉÎäÊżÄŁÓ����ŁŹÌ(zhšȘ)ÒâÒȘŚöÒ»Ïû·Àê ”Äê éLŁŹÈ»șóÄŚÔŒÒŽ°ôÏńïwÈË°ăÌűÜS”œÍâĂæ”ÄVöÉÏ����ĄŁĄ¶ËÀŒŸĄ·żÌź”ÄÊÇžžÓHĆcÒ»ČŒÉÌÔÚÄłÒčÍíŐÉúÒâ”Ä»îÓ���ŁŹÄǶYx”ĂîHÓĐčĆ”äζ”À���ŁŹ±ÆŐæÉńĂ۔ķŐúŚÈËÈçĆRÆäŸł���ĄŁÔÚĄ¶žžÓH”ÄŚîșóÒ»ŽÎÌӌߥ·ÖĐŁŹŚíŚ?nšši)„”ÄžžÓHÓÖŚłÉÁËÒ»Ö»Đ·����ŁŹ”«ÊÇŁŹŚîșó±»Öóß^șóÓÖÌÓÒĘÁË�ĄŁ
Ą¶ÓĂɳ©ŚöŐĐĆÆ”ÄŻđB(yšŁng)ÔșĄ·ÖĐŁŹžžÓHÏĘÈërég”Äćeλ îB(tš€i)���ŁŹŚśŒÒșĂÏńÏÓŐ곣”ÄrégŠžžÓHŐÛÄ„”ÄÁŠ¶ÈßČ»ò��ŁŹÓÖ°ŃËû§ßM(jšŹn)Ć€Çú”ÄrżŐ���ĄŁžžÓHÉúÁËÖŰČĄ»òŐßșžùŸÍÒŃœ(jš©ng)Č»ÔÚÈËÊÀŁŹŒÒÈË ĐĆVžæŐT»ó°ČĆĆËûÈ„ÁËÒ»ŒÒÓĂɳ©ŚöŐĐĆÆ”ÄŻđB(yšŁng)ÔșÖÎŻ���ĄŁąÊöŐ߳˻đÜ”œß@ÉńĂ۔įđB(yšŁng)ÔșÌœÍûžžÓH����ĄŁÄÇÀï”Äát(yš©)Éú·QËûÖÎŻ”ÄĂŰĂÜČ»ß^ÊÇ°ŃrégÜ»ŰÈ„ŁŹŚŽčËÀ”ÄÈËœèÓöțÊÖ”ÄrégÆŃÓŽ�����ĄŁß@ĐĄæ(zhššn)œ(jš©ng)łŁ°l(fšĄ)ÉúëxÆæ”ÄrżŐĆ€Çú��ŁŹąÊöŐßÜÜżŽ”œžžÓHÔÚï”êÀïŐĐŠïL(fš„ng)Éú���ŁŹżÉÊǻ۔œČĄÊÒșó
s°l(fšĄ)ŹF(xiš€n)ŃÙŃÙÒ»Ïą”ÄžžÓHÌÉÔÚŽČÉÏ���ĄŁŐûÆȘĐĄŐfâ·ŐêÉŁŹÏëÏóÆæÔ�����ŁŹÍŹrÓÖîHéżà��ĄŁ
ÓĐĐ©ŚśŒÒÏČg]ÎèÖűž«î^°ŃĐÎÈĘÔ~”ÄyíÏ€”(shšŽ)żł”ô���ŁŹ”«ÊÇÊæ ŽÄ
sĐĄĐÄÒíÒí”Ű°ŃÄÜòŒ(xšŹ)Äśß_(dšą)»ĂÏë”ÄĐÎÈĘÔ~Ò»Ò»ŐÙ»ŰíŁŹúŸÛÔÚŚÔŒșËÄÖÜ��ĄŁé_ÆȘ”ÄĄ¶°ËÔÂĄ·°Ń°ËÔ”ÄÔïáśß_(dšą)”ĂÈçŽËŸ«ÖÂ�ĄąÈçŽËșÚ°”ĄąÈçŽËÁîÈËÖÏÏąĄąÈçŽËÁîÈËżÖČÀ��ĄŁÇéč(jišŠ)șΔœoÒÔÍ(fšŽ)ŒÓ����ŁŹ”«ÊÇŠșÎËŰČÄ”ÄĂèÓÖÍ(fšŽ)ës”œÁîÈË°l(fšĄ)Öž”ÄłÌ¶ÈĄŁŚśŒÒÔÚÈçŽË¶ÌĐĄ”ÄÆȘ·ùÀïëSĐÄËùÓûșÍĂïÒśœy(tšŻng)Ő·š”œÈçŽË°ÁÂę”ÄłÌ¶È���ĄŁ”«ÊÇ���ŁŹËùÓĐß@Ò»ÇĐÓÖÊÇÔÚOÆäżbĂÜĄąÀ(yšąn)ĂC�ĄąÒ»œzČ»Æ”ÄżÌźÖĐÍêłÉ”ÄĄŁ°ËÔ”ÄÔïáÒČÊÇÓûÍû”ÄÔêÓ��ŁŹŚîșó�����ŁŹŚśéąÊöŐß”ÄÉÙÄêżŽÁ˱ížç°ŁĂŚ äżËĆÆÉÏ”ÄÂăówĆźÈËșóÉíów°l(fšĄ)ÉúÁËÒ»êĄÁÒ”Äđ(zhš€n)Àő���ŁŹžß¶ÈâżsșÍŸo”ÄÔêÓëSÖźáÈ»�ĄŁÎÒÒČëSÖűß@čÉșÒ֔ÎȻß^âí”ÄÔïáșÍÔêÓ”Äá·Ć¶űáÈ»��ĄŁ
Ą¶±©ïL(fš„ng)óEÓêĄ·ÓĂOÆäżä”ÄÊÖ·šĂèÁËÒ»F(tušąn)ËÁĆ°ÁËŐûŐûÈęÌìÈęÒč”ı©ïL(fš„ng)ĄŁŚśŐߊß@čÉżńïL(fš„ng)”ÄÁŠÁż�����ĄąÓ°í�����Ąą§(dšŁo)Ö”ĻĂÏë�ŁŹßM(jšŹn)ĐĐÁË·ÇłŁœk șÍŚĐÎ”ÄżÌźŁŹß@ӔĿÖČÀówòÔÚÎÒÍŻÄê”ÄžĐÓXÖĐȹȻőrÒ����ĄŁÈ»¶űŚśŐßÔÚ IÔìÁËß@·NżÖČÀâ·ŐșóÓÖëxÆæ”ŰíÁËÒ»čPŁșÇ°í¶ă±Ü±©ïL(fš„ng)”ÄÒÌÒòé°ą”ÂÀÁÇęÒ»Ö»č«ëu”ÄÓđĂ«șóÊÜ”œŽÌŒ€ŁŹâ”ĂÉíđ(zhš€n)Àő�ŁŹșúŃÔyŐZŁŹÓĂÉžùÄŸÆŹÎÆđÉíŚÓÔڔ۰ćÉÏyÌű��ŁŹŚîșóÔÚÒ»œÇÂäÀïżsłÉÒ»Žé»Ò a�����ĄŁ
Ą¶ŽșÌìĄ·”ÄčÊÊÂŸËśOéșÎ�ŁŹ”«ŚśŐßÔÚß@lÎŒ”ÄŸÉÏžœŒÓÁËožF”Ä|Îś���ĄŁß@ČżÖŠÂû·±Í(fšŽ)”ÄÖĐÆȘłäMÁËŠŒŸč(jišŠ)����ĄąŠ”ŰÏÂÊÀœçĄąŠËùÖ^čÊÊÂíÔŽ”Ű”ÄÆæËŒźÏë��ĄŁČ»țÓĐÌ«¶à”ÄŚśŒÒ»šÙMožF”ÄčPÄ«ŠÄłŒŸč(jišŠ)”ÄÒčÍíßM(jšŹn)ĐĐÈçŽËČ»
Æä©”ÄĂèÀL���ĄŁß@Đ©žĐÓX¶Œœ(jš©ng)ß^ŚśŐߔČĐÎÌÀí���ŁŹ”ĂÉńĂŰŸ_ûŁŹÉőÖÁłöÁËrżŐ”ÄĆ€Çú�����ĄŁ
Êæ ŽÄ”ÄÓĐĐ©ĐĄŐfœY(jišŠ)(gš°u)ÍêÈ«Č»îÈËÊìÏ€”ÄÌŚÂ·����ŁŹÒČÔSèŠè€»„ÒŁŹ”«ÊÇ�����ŁŹß@Đ©|ÎśŸÍÏńÓĐß
œÇ”ÄŐÛp
sÓÖș±Ò”ÄŐäÏĄà]Ʊ�ŁŹÊŐČŰŐßÜÜÖȘ”À���ŁŹ”«ÒÀÈ»ÛČ»áÊÖĄŁoŐÈçșÎ�����ŁŹÊæ ŽÄÊÇһλ„Žó”ÄŚśŒÒ�����ŁŹÀ(yšąn)ĂCŐJ(rššn)Őæ”ÄŚśŒÒ���ĄŁÎÒÔÚéŚxșÍ·Śg”Äß^łÌÖĐ����ŁŹ·Â·đżŽ”œÒ»ŁŚą”Ä”ńżÌŒÒÒ»ÈËÔÚéwÇÉÏ”ńŚÁÖűŚÔŒșÊÖÖДČśÆ·����ŁŹÒ»șÁĂŚÒ»șÁĂŚ”ŰÍÆßM(jšŹn)ÖűèŚÓŁŹÉúĆÂżłûÁËÊČĂŽ��ĄŁËûÊÇŐæŐę°ŃÎÄW(xušŠ)żŽŚśŚÔŒș”ÄÊÂÇé���ŁŹÎÄW(xušŠ)Śșő]ÓĐœoËû”ÄŹF(xiš€n)Éú»î§íÈÎșÎÊÀËŚ”ÄșĂÌ����ĄŁ
ß@±Ÿű·ŚgłöíșóRÖĂÁËąœüÈęÄê�����ŁŹŚîœKÄÜòłö°æßÒȘžĐÖxź(dšĄng)ÄêĐÂĐÇłö°æÉç”ÄÍßź(dšĄng)ÏÈÉú�ĄŁź(dšĄng)È»ŁŹßÒȘžĐÖxŚîÔç·ŚgÊæ ŽÄŚśÆ·”ÄÓÚÄŹÏÈÉú�����ŁŹÊÇËûŚîÔç°ŃÊæ ŽÄœéœB”œÖĐűí��ŁŹÔÚÎÒß@Đ©ÍâűÎÄW(xušŠ)ÛșĂŐßĐÄÖĐČ„ÏÂÏČg”Ä·NŚÓ��ŁŹÎÒÔÚß@ÀïÒČč§ŸŽ”Ű
ążŒÁËÓÚÄŹÏÈÉú·Śg”ÄÄÇŚÆȘ”ÄłÉčû��ĄŁ·Śgß^łÌÖДÔœĐÁ”Ï”ÄșܶàÍÖú���ŁŹß@λœđ°l(fšĄ)ĂÀĆźÍÎÒáÒÉœâ»órœ(jš©ng)łŁĆÔ՜ȩÒę���ŁŹÒ»î}”ÄŽđ°žËùÓĂÆȘ·ùČîČ»¶àÏàź(dšĄng)ÓÚÁËt¶ÌÎÄŁŹÔÚŽËÌŰÖÂÖxÒâ�Ą��ŁżÉϧ����ŁŹŹF(xiš€n)ÔÚ�����ŁŹĆcĐÁ”ÏʧȄÁËÂ(lišąn)Ï”����ŁŹËęÍÎÒœâŽđÒÉëy”ÄÎÄŚÖÒČ]ÓбŁŽæÏÂíĄŁŚîșó�ŁŹžĐÖxœÜÏÈÉúșͶàŒÓĐĄœăŁŹËûŽÙłÉß@±ŸĐĄŐfŒŻÔÚĐ”ijö°æÉçłö°æ����ĄŁÊæ ŽÄ”Ä»ȚïL(fš„ng)žńœoŚgŐߧí”Ä而śëy¶ÈÊÇżÉÏë¶űÖȘ”ÄŁŹŚgÎÄČ»ÈçÒâÄËÖÁʧŐ`ÖźÌżÏ¶šëyĂâ�ŁŹŚśéÔűœ(jš©ng)”Ä̜·ŁŹà(qušąn)ÇÒÁÄäÒ»žń����ĄŁ
Ą¶ÔÚéwÇȘ ÈfÎïĂÜŐZŁșČŒôÖZ·Êæ ŽÄÔÆȘĄ·ĐòŃÔ
ĐÄì`”ÄÄŹÆőĄąșôȘ(yš©ng)șÍŠÔ
žß??Ćd
ČŒôÖZ??Êæ ŽÄŁšBruno SchulzŁŹ1892ĄȘ1942Ł©ï@È»ÊÇčÂȘŐß�����ŁŹ”«ËûÊÇ„Žó”ÄčÂȘŐß���ĄŁ
ËûÔÚčÂȘÖĐŁŹÓĂÎÄŚÖșÍźéŚÔŒș(chuš€ng)ÁąÁËÒ»čČșÍű�����ŁŹÎÒ·QÖźéŁșô»ĂčČșÍű����ĄŁ
ŚxČŒôÖZ??Êæ ŽÄrŁŹÄăț°l(fšĄ)ÓXŚÔŒșČ»”ĂČ»rłŁÍŁîD����ŁŹËÆșőżĐèÒȘŐ{(diš€o)ŐûÒ»ÏÂÒŸàŁŹŐ{(diš€o)ŐûÒ»ÏÂč(jišŠ)Śà�ŁŹŚÔÈ»ÒČĐèÒȘŐ{(diš€o)ŐûÒ»ÏÂËŒŸSșÍĐÄB(tš€i)ŁŹČąČ»ÖśÒȘÊÇÒòéÉîW����Ąą»ȚŁŹ¶űžü¶à”ÄÊÇÒòéŃŁ��ĄŁÄÇĂŽœk ”ÄźĂæŁŹoß
”ÄÏëÏó�����ŁŹŃžŒŽ”ÄȚD(zhušŁn)Q����ŁŹÍ»È»”ÄÖĐàŁŹĂÜŒŻ�����ŁŹŽÌŃÛ����ŁŹ·ŽłŁŁŹÉńĂŰ���ŁŹËÙ¶È����ŁŹżŐ°Ś���ŁŹÌűÜS��ŁŹËùÓĐß@Ò»ÇĐÖ»ÄÜŚÄăžĐÓXŃŁ�ĄŁ”«ÍŁîDÆŹżÌÖźșóŁŹÄăœûČ»ŚĄÓÖţ̦ÆđÄżčâ�����ĄŁÄă”ÖőČ»ŚĄÄÇ”Àčâ”ÄŐT»ó�����ĄŁËû”ÄÎÄŚÖÖĐŽ_ÓĐÒ»”Àčâ�����ĄŁ¶űÄÇ”ÀčâŐŐÁÁ”ÄÊÇÒ»ÆŹȘÌŰ”ÄÌì”Ű��ĄŁ
ÏëÏóÁŠÔÚŽË°l(fšĄ)]łöÆæĂî”ÄŚśÓĂ�ĄŁŠÓÚŚśŒÒ¶űŃÔ�ŁŹÏëÏóÁŠÓĐrŸÍÊÇ(chuš€ng)ÔìÁŠĄŁŐęÊÇ{œèÏëÏó���ŁŹÊæ ŽÄżÊÇŚÎŚÎČ»Ÿë”ŰÄÈŐłŁșÍÆœÓčÖĐÌáÔÒâ����ĄŁËûłŁłŁÍšß^șÍŻ»òÉÙÄê”ÄÄżčâŽòÁżÊÀœçŁŹŐčé_ÏëÏó�����ĄŁÍŻÄêÄżčâ��ŁŹŒŐæ�����ŁŹŒ±ÆÈ�ŁŹoŸĐoÊűŁŹżÉÒÔ_ÆÆÒ»ÇĐœçÏȚ����ĄŁźŒÒÌìÙxÓÖŚËûŠÉ«ČÊO¶ÈĂôžĐŁŹœoÏëÏóÔöÌíÁ˱íŹF(xiš€n)ÓŽÎșÍżŐég�����ĄŁ
ß@Đ©¶ŒÊÇÔÒâ”ÄÏëÏó���ĄŁ
ÌÈÈôÊæ ŽÄHHÍŁÁôÓÚÔÒâ”ÄÏëÏó����ŁŹÄÇËûșÜÓĐżÉÄÜłÉéÒ»ĂûÀËÂțÖśÁxŚśŒÒĄŁ”«Ëûï@È»ÓÖÍùÇ°ŚßÁËÒ»Čœ�ĄŁß@Ò»ČœÖÁêP(gušĄn)ÖŰÒȘŁŹÓÖÒâζÉîéL����ŁŹÊÇÙ|(zhšŹ)”ÄïwÜSĄŁÊÂÉÏ���ŁŹËûÔÚČ»àÌáÔÒâ��ŁŹÒČÔÚëSrŽĘ§ÔÒ⥣ȘqÈçĆźÉń”Ä°ą”ÂÀżÉÒÔÓĂÒ»°ŃßÖă»òÒ»ÊÖĘőŚĄžžÓH”Ä»ĂÏëÊÂI(yšš)��ĄŁ¶űžžÓH�����ŁŹĄ°ÄÇČ»żÉŸÈ˔ČŽĆdÔÈË�ŁŹÄÇźÏëÌìé_”ÄŠĐg(shšŽ)ŽóĄ±ŁŹÓÉÓÚÉúĂüÁŠ”ÄË„œß���ŁŹÓÉÓÚ·N·NÈ(nšši)ÔÚșÍÍâÔÚ”ÄÒòËŰ�ŁŹÍŚłÉÁ˶dúĄąóŻòëșÍóŠĐ·����ĄŁÏà·ŽŁŹŚßœüÁËżŽ���ŁŹč·ŸčÈ»ÊÇÈË��ĄŁÏëÏóÒò¶ű«@”Ăżá
sÓÖŒ€ÁÒ”ÄÙ|(zhšŹ)”Ű��ŁŹÉÏÉę”œô»Ă����ĄąÉńÔșÍÔąŃԔĞ߶È��ĄŁÔÚÉńÔșÍÔąŃÔÖĐ��ŁŹß
œçÏûłę�ŁŹŚÔÈ»Ò(guš©)tŚÎ»ÓÚÈ(nšši)ĐÄĐèÇóĄŁÈ(nšši)ĐÄ����ŁŹŸÍÊÇŚîžß·štŁŹŸÍÊÇŚîžßŐæ�����ĄŁß@îDrŚËû”ÄŚś«@”ĂÁËâÓô”ÄŹF(xiš€n)ŽúÖśÁxÌŰŐśĄŁËûߟ«ÍšŐZŃÔ”ÄħÁŠ�ĄŁŠÓÚËûŁŹŐZŃÔŒÈÊÇÉńÔ���ŁŹÒČÊÇŚÚœÌ����ĄŁŐZŃÔ”ÄħĐg(shšŽ)ÍÖúËûÉîÈëÊÀœç”Äô»Ă��ŁŹŚîœKąÆœÓčșÍžŻĐà»ŻéÉńÆæ��ĄŁ
ÎÒÒ»Ö±ÔÚÏëŁșČŒôÖZ??Êæ ŽÄ”ÄÒâÁxșÍrÖ”ŸżŸčÔÚÄÄÀï�����Łż
ČŒôÖZ??Êæ ŽÄ”ÄÒâÁxșÍr֔ǥǥÔÚÓÚ����ŁŹą°l(fšĄ)ÎÒ?nšši)çșÎȚD(zhušŁn)ÏòÈ(nšši)ĐÄ����ŁŹȚD(zhušŁn)ÏòÓîÖæÉîÌ�����ŁŹÈçșÎœ(jš©ng)ÓÉÏëÏó�����Ąąô»ĂșÍŚĐÎ(gš°u)œšŚÔŒș”ÄÉńÔ�����ŁŹÈçșÎąÆœÓč�ĄąȘMĐĄșͻҰ”ȚD(zhušŁn)ŚłÉŽÌÈËĐÄÄc”ÄÉńÆæ��Ąąß|éșÍÓÀșă�ĄŁ
±ŸÙ|(zhšŹ)ÉÏŁŹČŒôÖZ??Êæ ŽÄÊÇλÔÈË��ŁŹ„Žó”ÄÔÈË����ĄŁß@Ò»ücÖĐűÔÈËĄąÉąÎÄŒÒșÚÌŐĂôäJ”Ű°l(fšĄ)ŹF(xiš€n)ÁË�ĄŁČ»HH°l(fšĄ)ŹF(xiš€n)ŁŹËûßÒȘłÊŹF(xiš€n)�ŁŹĄ°ÓĂhŐZÔžè���ŁŹłÊŹF(xiš€n)ÁíÒ»ČŒôÖZ??Êæ ŽÄĄ±ŁŹČą
ąĆcĄ°ČŒôÖZ??Êæ ŽÄ”ÄÎÄW(xušŠ)ÉúĂüĄ±�ĄŁ
ÓÚÊÇŁŹĄ¶ÔÚéwÇȘ ÈfÎïĂÜŐZŁșČŒôÖZ??Êæ ŽÄÔÆȘĄ·�ŁŹÒ»ČżÉńÆæ”ÄÎıŸŁŹÆæÛE°ăŐQÉú���ĄŁ
ëHÉÏ����ŁŹß@ÊÇһλÔÈËÔÚÏòÁíһλÔÈËÖŸŽ����ŁŹ»òŐßŐfһλÔÈËÔÚÏòÓÀșășÍoß
”ÄÔÒâÖŸŽĄŁß@·NÖŸŽoÒÉÒâζÖűÉîżÌ”ÄÀíœâ����ŁŹÉîżÌ”ÄÙÙpŁŹÉîżÌ”ÄÏໄąÊŸ��ŁŹÉîżÌ”ÄĐÊĐÊÏàϧ�ĄŁÉőÖÁßČ»ÖčÓÚŽË�ŁŹžüÊÇíŚÔ|Îś·œ”ÄÉλÔÈËËĐg(shšŽ)șÍĐÄì`ÉÏ”ÄÄŹÆő��ĄąșôȘ(yš©ng)șÍŠÔ���ĄŁß@Ó”ÄÄŹÆőĄąșôȘ(yš©ng)șÍŠÔ��ŁŹÒŃœ(jš©ng)(gš°u)łÉÒ»·NOÖ”Ļ„ÎÄ�����ŁŹÉą°l(fšĄ)łöËĐg(shšŽ)șÍĐÄì`ĂÔÈË”ÄčâÉ�ĄŁ
șÚÌŐŐfŁșĄ°ÔÚÎÒËùáÛ”ÄhŐZÊÀœçŁŹœèÖúÎÒĐÄ�ĄąÎÒÊÖŁŹÄÜòŚźű”Äß@λǰĘ
ŚśŒÒ����ŁŹÒÔÔ”ÄĐÎÊœĄąÒÔÔÈË”ÄÉí·ĘÍ(fšŽ)»îÒ»ŽÎ��ŁŹÎÒ����ŁŹ±¶žĐsĐÒĄŁĄ±
ÒòŽË���ŁŹÎÒÏàĐĆ�ŁŹŚxČŒôÖZ??Êæ ŽÄ�����ŁŹÔÙŚxșÚÌՔĥ¶ÔÚéwÇȘ ÈfÎïĂÜŐZŁșČŒôÖZ??Êæ ŽÄÔÆȘĄ·��ŁŹ»òŐß���ŁŹŚxșÚÌՔĥ¶ÔÚéwÇȘ ÈfÎïĂÜŐZŁșČŒôÖZ??Êæ ŽÄÔÆȘĄ·�ŁŹÔÙŚxČŒôÖZ??Êæ ŽÄ�ŁŹÎÒ¶ŒțÓĐo±M”ÄÆڎ꣏ÎÒÒȶŒțÔâÓöo”(shšŽ)”ÄžĐÓ��ŁŹÒ»¶š”Ä��ĄŁ
2017Äê7ÔÂ9ÈŐÓÚ±±Ÿ©
ŁšžßĆd�����ŁŹÔÈË����ŁŹ·ŚgŒÒŁŹĄ¶ÊÀœçÎÄW(xušŠ)Ą·ÖśŸŁ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