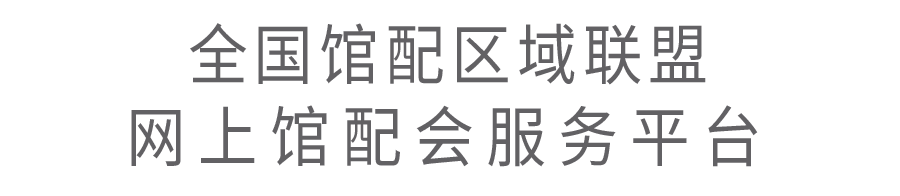ÐōŌŧ
ķĄ|
ĄķÆßĮ§ĀïÁũÍöĄ·ĘĮŌŧąūēŧĪģĢĩÄŧØäĄĢŨũÕßĒŋÉÄÁÏČÉú1920ÄęģöÉú�����ĢŽ1937ÄęÆßÆßĘÂŨr(shĻŠ)ĘŪÆßq�ĢŽĘĮÉ―|ĘĄÁĒĩÚŌŧÖÐW(xuĻĶ)W(xuĻĶ)ÉúĄĢŌō?yĻĪn)éūÜ―^ÔÚČÕŋÜ―y(tĻŊng)ÖÎÏÂß^ÍöøÅŦĩÄÉúŧî�����ĢŽÔÐĢČý°ŲķāÃûÉúÔÚÐĢéLO|Éú§îI(lĻŦng)ÏÂ���ĢŽīĐÔ―šÓÄÏ�ĄĒšþąąĄĒęÎũ��ĢŽŨîšóĩ―ß_(dĻĒ)ËÄīĻūdę��ĢŽ°ÏÉæÆßĮ§Āï����ĢŽvr(shĻŠ)ČýÄęķāĄĢĶÓÚČËÉúķøŅÔ���ĢŽšÍÆ―°ēĩÄÉúŧîĘĮģĢČËĩÄŨ·Įó��ĄĢĩŦĶÓÚÓķøŅÔ���ĢŽ·ĮģĢ îB(tĻĪi)ĩÄ―(jĻĐng)vÁôÏÂĩÄÓĄÏóÍųÍųļüÉîĄĢĖØĘâĩÄÁũÍö―(jĻĐng)v��ĢŽŨĒÏČÉú―KÉúëyÍü�ĄĢđÅÏĄÖŪÄęĢŽËûÍęģÉÁËŌŧēŋķþĘŪÓāČfŨÖĩÄŧØä�ĢŽÔž(xĻŽ)ÓäÁËß@ķÎČËÉúđĘĘÂĢŽēĒīōÓĄģÉÔ����ĢŽÕũĮóÆäËûŪ(dĻĄng)ĘÂČËšÍÖŠĮéÕßĩÄŌâŌ�����ĢŽÓÐŨRÕßžž―oÓčšÃÔu��ĄĢ2007Äę��ĢŽĒŋÉÄÁÏČÉúēĄđĘ�ĄĢīËø―üÆÚžīĒģö°æ����ĢŽÕÜËÃĒļýŨÓÏĢÍûÎŌŌŧÆŠÐōŅÔ���ĢŽÎŌēŧÄÜÍÆ
sËûĩÄÃĀŌâ�����ĄĢ
ÓÕß@ąūøĩÄČ(nĻĻi)ČÝÖŪĮ°�ĢŽÏČŌŠÓÕŌŧÏÂÖÐW(xuĻĶ)―ĖÓýÔÚēŧÍŽr(shĻŠ)īúĩÄÆÕž°ģĖķČĄ��ĢŽF(xiĻĪn)ÔÚÖÐøČËĩÄŨî―KW(xuĻĶ)vČįđûĘĮÖÐW(xuĻĶ)����ĢŽþąŧÕJ(rĻĻn)éW(xuĻĶ)vĩÍĄĢĩŦÃņøÄęīúĮérēŧÍŽĄĢÖÐøŽF(xiĻĪn)īúW(xuĻĶ)ÐĢ―ĖÓýÆðÔīÓÚĮåģŊÄĐÄę����ĄĢĩ―ÃņøÄęīúĢŽđŦÁĒW(xuĻĶ)ÐĢĩ(shĻī)ÁŋČÔČŧēŧķā���ĢŽŌŧ°ãĘĮŋhĀïÞkÐĄW(xuĻĶ)����ĢŽĘĄĀïÞkÖÐW(xuĻĶ)�����ĢŽøÁĒĩÄīóW(xuĻĶ)ĮüÖļŋÉĩ(shĻī)���ĄĢžÓÉÏË―ÁĒšÍ―ĖþĩÄW(xuĻĶ)ÐĢ���ĢŽĩ(shĻī)ÁŋČÔČŧÓÐÏÞĄĢĒÏČÉúŋžČĄĩÄÉ―|ĘĄÁĒĩÚŌŧÖÐW(xuĻĶ)�ĢŽūÍĘĮŪ(dĻĄng)r(shĻŠ)ÔĘĄW(xuĻĶ)ŨÓēÄŋĩÄšÕšÕW(xuĻĶ)ļŪĄĢŪ(dĻĄng)r(shĻŠ)ÖÐW(xuĻĶ)ÉúÔÚŋ?cĻĻ)ËŋÚÖÐËųÕžĩÄąČĀý�ĢŽąČ―ņĖėŅÐūŋÉúÔÚŋČ(cĻĻ)ËŋÚÖÐËųÕžĩÄąČĀýßĩÍĄĢËųŌÔÄĮr(shĻŠ)ĩÄÖÐW(xuĻĶ)Éú���ĢŽūÍËãĘĮÏāĶÏĄČąĩÄÎÄŧŊČËÁË��ĢŽÄęýgŌēÝ^―ņĖėĩÄÖÐW(xuĻĶ)Éúé�����ĄĢķøŪ(dĻĄng)r(shĻŠ)ĩÄÖÐW(xuĻĶ)―Ė����ĢŽÅcr(shĻŠ)ÏÂŌāÓÐēŧÍŽĄĢÍíĮåĩ―ÃņģõÄĮŌŧÅúÕÆÎÕÐÂW(xuĻĶ)ĩÄÖŠŨRČË��ĢŽËûĩÄĩÜŨÓŌŅ―(jĻĐng)ŋÉŌÔŨßÉÏ―ĖĩÄÎŧ����ĄĢÆäÖÐÓÐĩÄŋÉ·QÖøÃûW(xuĻĶ)Õß�����ĢŽĩ―ÖÐW(xuĻĶ)ČÎ―ĖĩÄĮérēĒēŧõrŌ����ĄĢĒŋÉÄÁÏČÉúĩÄČÎÕnĀÏÖÐĢŽĀîVĖï�ĄĒęÏčúQķžĘĮøČ(nĻĻi)ÖŠÃûĩÄW(xuĻĶ)Õß����ĄĢÆäËûķāÎŧ―ĖÔÚÖÐČAČËÃņđēšÍøģÉÁĒŌÔšó�����ĢŽŌēžžÔÚīóW(xuĻĶ)ú(dĻĄn)ČÎ―ĖÂ�����ĄĢĒŋÉÄÁÏČÉúŌōÓHÖËÓÚĀîVĖïĀÏ�ĢŽķøÔįÔįĩĮÉÏÁËÎÄŊĢŽēĒðB(yĻĢng)ģÉÁË―KÉúŨũĩÄÁ(xĻŠ)T���ĄĢÄß@Ōŧüc(diĻĢn)ÉÏÕf����ĢŽĒÏČÉúŋÉÖ^ÔįĘėķøÐŌß\(yĻīn)����ĄĢ
Ōō?yĻĪn)éĀÏĩÄÓ°íĢŽÉÐÔÚģõÖÐëAķÎĩÄĒŋÉÄÁūÍÏōÍųŅÓ°ē��ĢŽÏōÍųÖÐđē�ĄĢß@ģÉéŧØäĩÄŧųąūĩŨÉŦ����ĄĢŪ(dĻĄng)r(shĻŠ)ĩÄąģū°ëmČŧĘĮøđēšÏŨũ�ĢŽđēÍŽŋđČÕĢŽĩŦühÅÉĩÄÄĶēÁ��ĢŽēŧÍŽËžģąĩÄēîŪ���ĢŽÉîÉîĩØÓ°íÖøÓĘĩÄÁũÍöÉúŧî��ĄĢĒÏČÉú°ŅÖÐW(xuĻĶ)r(shĻŠ)īúīóów·ÖģÉÉķÎ�ĄĢĮ°ŌŧķÎĘĮÉ―|ĘĄÁĒÖÐW(xuĻĶ)šÍøÁĒĩÚÁųÖÐW(xuĻĶ)ĩÚËÄ·ÖÐĢ����ĢŽŌō?qĻą)O|ÉúĄĒšúļÉĮā�ĄĒķĄÓÃŲeĄĒĀîVĖïĩČÐĢéL�����ĄĒĀÏÖũ§(dĻĢo)ÖøW(xuĻĶ)ÐĢĩÄŨßÏō�����ĢŽ―oËûÁôÏÂÁËÃĀšÃĩÄŧØ��ĄĢšóŌŧķÎÍęČŦēĒČëøÁĒĩÚÁųÖÐW(xuĻĶ)��ĢŽÕÆŋØÐĢ@ĩÄŌēģÉéøÃņüh·―ÃæÖą―ÓÎŊČÎĩÄđŲÁÅ����ĢŽÏōÍųŅÓ°ēĩÄĒŋÉÄÁĩČW(xuĻĶ)ÉúąãĖÓÚÎĢëU(xiĻĢn)ÖŪÖÐĢŽW(xuĻĶ)ÐĢŌēģÉéËûĩÄØŽô��ĄĢĒÏČÉúŅÖøß@ÓĩÄĮéļÐ�����ĢŽÖvĘöŪ(dĻĄng)ÄęĩÄđĘĘÂ�����ĢŽÔSķāž(xĻŽ)đ(jiĻĶ)ó@ÐÄÓÆĮ�����ĄĢļüÓÐŌâÎķĩÄĘĮ��ĢŽŌŧÐĐŪ(dĻĄng)ĘÂČËÍíÄęšÍĒÏČÉúÔŲīÎÏā·ę����ĢŽŧØäÖÐ―ŧīúÁËÏāęP(guĻĄn)ĀÏ��ĄĒÍŽW(xuĻĶ)šó°ëÉúĩÄÃüß\(yĻīn)����ĄĢ
ÎŌŨxÁËß@ēŋŧØä����ĢŽßÏëQŌŧ(gĻĻ)Ō―ĮĢŽŌąūøÍļÂķĩÄČýËÄĘŪÄęīúÖÐø―ĖÓýÉúB(tĻĪi)·―ÃæĩÄÐÅÏĒ����ĄĢß^ČĨĢŽÖÐđēÔÚŋđČÕð(zhĻĪn) ÖÐĩÄÞkW(xuĻĶ)ŧîÓĘĮühĘ·ÕũžŊšÍŅÐūŋĶÏó�����ĢŽĩÃĩ―Ý^éģä·ÖĩÄÍÚūō���ĄĢ―ü20Äęí���ĢŽÏņÎũÄÏÂ(liĻĒn)īóß@ÓīúąíÖÐøð(zhĻĪn)r(shĻŠ)―ĖÓýļßķËĩÄC(jĻĐ)(gĻ°u)ŌēĩÃĩ―W(xuĻĶ)―įĩÄęP(guĻĄn)ŨĒ����ĢŽŅÐūŋŌŅģÉï@W(xuĻĶ)����ĄĢÏāĶíÕf��ĢŽÏņÉ―|ĘĄÁĒÖÐW(xuĻĶ)ŧōøÁĒĩÚÁųÖÐW(xuĻĶ)ß@Óø―y(tĻŊng)
^(qĻą)ĩÄW(xuĻĶ)ÐĢ�����ĢŽŅÐūŋūÍąČÝ^ąĄČõ��ĄĢĒļýŨÓÔÚīúšóÓÖÐÕf���ĢŽĄ°øÁĒĩÚÁųÖÐW(xuĻĶ)ĩÚËÄ·ÖÐĢĢĻŌÔĘĄÁĒŌŧÖÐéÖũówĢĐÔÚ°ēÐĢËÄīĻÁ_―ŌÔšó�����ĢŽÉúÔøģöß^ĄŪÁũÍöŧØĄŊ����ĢŽMŋŊÓĄģö°æ�ĢŽøÃûĄķÆßĮ§ĀïÕũģĖĄ·ŧōĄķÔÚïL(fĻĨng)É°ÖÐĮ°ßM(jĻŽn)Ą·ĢŽÓÉO|ÉúĄĒęÏčúQ����ĄĒĀîVĖïĩČĀÏūÝÍęģÉĢŽšóøļåūđēŧÉũGʧ�����ĢŽÎīÄÜÃæĘĀ��ĄĢĖîŅa(bĻģ)ß@(gĻĻ)ȹʧĘĮļļÓHÍíÄęĩÄŌŧīóÐÄÔļĄą�����ĄĢĩÄī_����ĢŽČËîvĘ·ÄÜąŧÓäÏÂíĩÄÖŧĘĮšÜÉŲĩÄŌŧēŋ·ÖĢŽļüķāĩÄķžąŧäÎ]ÁË����ĄĢß@ąūŧØäÄÜōÍęģÉĢŽĮŌÄÜģö°æ����ĢŽßM(jĻŽn)ČëđŦđēŌŌ°���ĢŽÆäĖîŅa(bĻģ)vĘ·ŋÕ°ŨĩÄŌâÁxēŧŋÉĩÍđĀĄĢ
ÔÚŨũÕßÍŧģöĩÄÖũūÖŪÍâ���ĢŽÎŌßÓÐŌÔÏÂŨüc(diĻĢn)ļÐÓ|šÍÂ(liĻĒn)ÏëĢš
ÆäŌŧĢŽð(zhĻĪn)r(shĻŠ)ÕþļŪØ(cĻĒi)ÕþĩÄ―ĖÓýÖ§ģöĘĮŌŧ(gĻĻ)ÉÐīýŅÐūŋĩÄÕnî}��ĄĢĒŋÉÄÁŪ(dĻĄng)r(shĻŠ)ĘĮŌŧ(gĻĻ)ģõÖÐÉú����ĢŽß@·―ÃæĮérÕÆÎÕēŧķāĢŽĮéÓÐŋÉÔ�ĄĢøĖáĩ―ÁËW(xuĻĶ)ÐĢ ČĄØ(cĻĒi)ÕþÖ§ģÖĩÄĮérĢŽŌēĖáĩ――ĖĮ·Ð―ŽF(xiĻĪn)Ïó�ĄĢĩŦŌŧÐĐž(xĻŽ)đ(jiĻĶ)ąíÃũĢŽÁũÍöÉúĩÄ―(jĻĐng)ú(jĻŽ) îrČÔÝ^Ū(dĻĄng)?shĻī)ØÞr(nĻŪng)Ãņé(yĻu)��ĄĢŨũÕßĘĮëxé_W(xuĻĶ)ÐĢĖÓÍöēÅļÐĩ――(jĻĐng)ú(jĻŽ)ĩÄĀ§ū―�ĄĢČįđûÓÐíŨÔØ(cĻĒi)ÕþÖ§ģö·―ÃæĩÄŌŧĘÖēÄÁÏĢŽūÍļüšÃÁË���ĄĢ
Æäķþ��ĢŽŨðÖØ―ĖÓýČÔĘĮŪ(dĻĄng)r(shĻŠ)ĩÄÉįþïL(fĻĨng)â�����ĄĢŌŧËųÍâĘĄÖÐW(xuĻĶ)��ĢŽÁũÍöÆßĮ§Āï��ĢŽŌŧ·îÅæÁũëx��ĢŽĩŦÔÚŅØÍūļũĩØŧųąūÉÏķžÄÜĩÃĩ―ÉÆīýšÍ°ēÖÃ�ĄĢŋÉŌŨðÖØ―ĖĩÄÖÐøũ―y(tĻŊng)ĀíÓ^ÔÚŋđð(zhĻĪn)ÄęīúēĒÎīāÁŅ����ĄĢ
ÆäČýĢŽW(xuĻĶ)ÐĢëmÔÚÁũÍö îB(tĻĪi)���ĢŽČÔČŧūSÏĩÁËÏāĶÍęÕûĩÄÕnģĖÔO(shĻĻ)ÖÃ�����ĄĢé_ÔO(shĻĻ)ĩÄÕnģĖŋÉ·QÎÄĀíūãČŦ�����ĢŽÓÐøÎÄ���ĄĒvĘ·���ĄĒĩØĀíĄĒÓĒÕZ��ĄĒĩ(shĻī)W(xuĻĶ)�ĄĒÎïĀí�ĄĒŧŊW(xuĻĶ)ĄĒÉúÎï��ĄĒówÓý���ĄĒŌô·�ĄĒÃĀÐg(shĻī)�ĄĒđŦÃņĩČÕnĢŽëmČŧ―ĖW(xuĻĶ)ЧđûēŧŌŧ����ĢŽŨũÕßĶēŧÍŽ―ĖļũÓаýŲHĢŽĩŦķāĩ(shĻī)―ĖķžĘĮīóW(xuĻĶ)Ū
I(yĻĻ)�ĢŽÆäÖÐēŧÉŲßĘĮÃûÅÆīóW(xuĻĶ)Ū
I(yĻĻ)ĢŽŠ(yĻĐng)Ū(dĻĄng)ÕfŲYËŪÆ―ŋÉÓ^����ĄĢ
ÆäËÄ����ĢŽÁũÍöÖÐW(xuĻĶ)ÉúĩÄÕnÓāÉúŧîÏāŪ(dĻĄng)ØSļŧ���ĢŽÓÐÉįF(tuĻĒn)�����ĢŽÓÐąÚó(bĻĪo)��ĢŽÓÐówÓýąČŲ�����ĢŽßÄÜ―MģÉĄF(tuĻĒn)đŦé_ŅÝģö���ĄĒÏōđŦąÐûũŋđČÕĢŽŋÉŌČŦÃæŋđð(zhĻĪn)ģõÆÚëAķÎËžÏëÎÄŧŊĩÄŧîÜS��ĄĢ
ŌÔÉÏ·―ÃæēĒ·ĮŧØäÖÐŋĖŌâÕÃï@�ĢŽĩŦÎŌŨxšóßĘĮļÐĩ―ÖĩĩÃĖ―ūŋĄĢ
2019Äę8ÔÂ
Ðōķþ
OūSÔĀĢĻ|ÉúĢĐ
ĘŪķþÔÂÉîŌđĀïeÁËĖĐÉ―�����ĢŽ
ĘŪķþÔÂÉîŌđĀïÓÖķÉÁËh―ĄĢ
ÎŌ?nĻĻi)ý°ŲČËŌŧ(gĻĻ)ÎĒÐĶĄŠ
ĶÖø�ĢŽ
īëU(xiĻĢn)ĩÄēĻýĢŽ
oĮéĩÄïL(fĻĨng)ËŠ�����ĄĢ
ĘŪķþÔÂÉîŌđĀïĖÓģöĖĐ°ē�����ĢŽ
ĘŪķþÔÂÉîŌđĀïëxé_āyę����ĄĢ
ÎŌÆßĮ§ĀïŌŧ(gĻĻ)ē―·ĨĄŠ
°ÏÉæ���ĢŽ
ÔÚšÚ°ĩĀï���ĢŽęÔúĢŽ
ÏōÖøŨÔÓÉ��ĢŽ
ÏōÖøđâ���ĄĢ
1939Äę7ÔÂ23ČÕ
ë[ë[ĩÄÅÚÂÖÐé_W(xuĻĶ)ĄĄ/001
ßwÐĢĖĐ°ēĄĄÔâŋņÞZEÕĻĄĄ/017
Í―ē―ôÎũÄÏĄĄ/033
ÝÞD(zhuĻĢn)Ą°ë]šĢÆ―hĄąšŦÔSēýĄĄ/050ŲdÆėĩꥥ/061
ŋņïjūČÍöđĪŨũF(tuĻĒn)ĄĄ/072
ÔĨķõß
ÓöÆæĄĄ/085
É―ģĮāyęh―ģÁīŽĄĄ/093
ÐĢéLÂŅÔČĨęąąŋžēėð(zhĻĪn)r(shĻŠ)―ĖÓýĄĄ/101
Ą°―ęĘĮŌŧlýĄąĄĄ/109
ĄķŨÏČûĄ·ĄĄÓáÐÂÃņČĨęąąĄĄ/115
úđĨ―ĖģóĄĄĄ/126
ŌđŨßāyęģĮĄĄ/137
Ë{(lĻĒn)ĐëU(xiĻĢn)ÆæĄĄ/145
äęŋhéLĄĄ/156
ēĄÁôhÖÐĄĄ/164
ĮāŅōóAŌđÔžtÜĄĄ/174
ĶéTÐÛęP(guĻĄn)ĄĄ/183
Á_―ËÄ·ÖÐ�����ĢĄĄ/192
ūdęģõĩ―ŋÐ��ĢĄĄ/203
Ą°ühŧŊ―ĖÓýĄą―MŋđÜŋØĄĄ/216
Ą°ĩÚÎå·ÖÐ����ĢĄąĘĮŌŧÆŽöĄĄ/225
ŧŊW(xuĻĶ)ąøF(tuĻĒn)ĄĄ/242
ÏōÍųŅÓ°ēôËĄĄ/250
ÎÄĮäĩÄÔâëHĄĄ/265
VĖïĩÄÎÄW(xuĻĶ)―ĖÕdĄĄįČĨÄÏŅóĄĄ/277
ô[ÕnĘžþĄĄ/289
ówÓýĘĒĘÂŨ―·ÅÐĄŲ\ĄĄ/297
Ą°Íâú―MŋĄąĄŠĄŠŨxøþĄĄ/308
ÖŧÉíëxÐ�����ĢĄ°ÄļÐ�ĢĄąÔŠĩĐÍíþĄĄå\đŲģĮĄĄ/316
žÄËÞÉáÚÓ IęÏčúQĄĄ/332
ķãąÜŨ·ēķŌšýŋÚĄĄ/345
Ą°ąÜģðÍķÓHŨßë]ĮØĄąĄĄ/358
ēŧĮüĩÄŌŧČšĢĻīúšóÓĢĐĄĄ/373